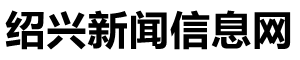作者:陈永新
二0二四年三月三日
序

只要是心智健全的人,对于故乡的朴素感情总是与生俱来的,也是挥之不去的。
我自十六岁少小离家奔县城谋生,二十五年后又进杭州、闯京城,兜兜转转,心中最牵挂的,仍然是那生我养我的故土江藻镇江藻村。人在异乡时,晚上屡屡闯入梦境的,却依然是孩提时代小伙伴们捉迷藏的村口那株大樟树。
故乡江藻,就像一块无形的巨大磁铁吸引着我。二十来岁时,周末每每从茶厂下班时县城到江藻的汽车票已卖完,那时还买不到也买不起自行车,三十四华里的路程,咬咬牙就沿着公路走回江藻,中间有拖拉机开过就不顾拖拉机手呵斥强行扒上去搭一段,灰头土脸三个多小时走到江藻,看到老娘一脸心疼地端上热水洗脸,一身疲惫便烟消云散,顿觉温馨无比……
及至后来有了自行车、摩托车、轿车,练手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大脑发出的指令方向一定是路况算差的诸姚公路,因为那里指向的是江藻。
哪怕现在已年逾花甲,下午五点左右,开起车,却常常几乎是鬼使神差地往江藻开,因为那里的小饭馆里的青菜是江藻父老地里种的,特别糯软,咬下去口唇生香……
江藻两字,已溶入血液中。
这几年写了几篇诸暨几个地方的文章,有我曾短暂读书过的姚公埠、茶厂派往收茶叶的马剑,去当人小鬼大职工学校老师的赵家山口,更有与江藻近在咫尺的流光溢彩珍珠小镇山下湖,有许多朋友来问:怎么不写一下感情最深的江藻?
我无言以对。爱至深,忧至切,触目伤怀大概是我久久不愿动笔写江藻的原因。
今天忽然想写了,就将江藻的几个小片段集结一下写篇小文。较之我对江藻的感情,当然是挂一漏万。
江藻湖

江藻湖,是江藻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它是诸暨最大的天然池塘,我们儿时,江藻湖水域120亩,外侧是一条风水埂,堤埂上矗立着一排十多株树干已空心,树身仍枝繁叶茂的百年香樟树,内侧是半塘天然生成的莲藕,春夏之时,樟树的香气和荷花的清香便弥漫在小镇的上空,一幅江南水墨画浑然天成。
六十年代,曾有在郑州铁路局工作的江藻人向同事们描绘起江藻美景,便充满自豪地说:我的家乡江藻就像图画里一样。引得郑州同事心驰神往。
江藻湖的来历颇有传奇色彩。
明万历年间,江藻有一位进士,而相邻之墨城坞却有七个进士,墨城坞人觊觎这美丽的江藻湖,便由七进士起头向县衙告状,要求判明江藻湖权属归墨城坞。那县官当众架起一口油锅,油沸腾后掷入一铁秤砣,称“自家的东西任谁也不会放弃,谁先捞起江藻湖便归谁”。此言一出,墨城坞七进士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前,江藻的钱氏进士却毫不犹豫,伸手从油锅中捞出秤砣。
江藻湖的权属就此尘埃落定。钱进士的手臂却因烫伤烂断终致不治。江藻民众感念其忠义,将其葬于江藻湖正中,四周种上杨柳。我儿时常常亲眼目睹那湖中央的依依垂柳在风中摇曳。
“巍峩明镜丽江藻,龙山麓,雁池滨,双池桃李新,鹫鱼悟天真……”
——从四十年代的江藻小学校长、被江藻人尊呼为“天老权”的江藻小学校长钱天权先生所作的校歌中,依稀还可见江南水墨画中的江藻款款走来……
山有龙头伴凤凰,
湖在镇中称江藻,
钱氏一脉居千载,
桃李春风笑南庄。
这是我最亲近的兄弟、与我一样喝江藻湖水长大的发小多年前描写江藻的诗,江藻有龙头、凤凰、南庄三山,都被他轻松嵌入诗中,足见才情。
只可惜,龙头凤凰依旧,我心中桃李春风已不再笑南庄。
儿时相伴嬉耍于江藻湖边天真无邪,青年时共同漫步于江藻湖边豪情万丈想为江藻父老争光添彩的情景,时时入得梦来……
江藻湖此前自生自灭,流失、蚕食近三分之一,后经整治疏浚,面目焕然一新,但不知何故,引经据典,将江藻湖恢复命称为雁宿湖。
江藻民众对此却不以为然,几十代口耳相传,本地人叫江藻湖,江藻以外的人叫江藻大塘,已是无法更改也不必更改的称呼。
面对江藻湖,难掩触目伤怀,江藻!江藻!生我养我的故乡,无处安放的忧伤!
溪坑埠头、乳娘

去年大年二十,去江藻下陈自然村参加吃奶兄弟(幼时乳娘儿子,因1963年老娘在外乡教书无法喂乳,将我托付乳娘处喂奶)娶儿媳婚宴。
幼时天天玩耍的溪坑埠头,溪水依旧,时光倏忽六十余载,不胜感慨……
见到几位小时候背我玩耍的姐姐,她们已远嫁,多年未见,诉说我幼时情景,当她们拉着手叫我乳名,亲热万分时,眼眶竟已湿润……
吃奶兄弟倒一直有往来。1996年,他结婚是我开我的老奔驰作婚车,二十八年后,却成了长辈,喝他儿子喜酒,他也不好意思再让我这个小老头开婚车了。

祖宅

江藻老街上,我孩提时代的祖宅。前几天在江藻晚饭后特意踱到此处,旧时痕迹犹在,物是人非,当年辛酸场景涌上心头,直欲欷歔……
楼下半间为我一家六口灶间兼吃饭间,逼仄局促自不待言,风雨如磐年代,门楣上被强制挂着的是“历史反革命陈XX”木牌,被责令每年大年三十自行更换或加深墨迹,老父站在凳子上用鎯头钉木牌时,我在下方扶着凳子以免摔倒。屈辱场面,刻骨铭心。
楼上为一家蜗居处,家徒四壁,父亲劳作一天,晚上用煤油灯罩烫灭蚊帐内蚊子情景犹在眼前……
站在老宅前,难掩如潮水般袭来的伤感情绪。
俱往矣!所幸的是:那个人妖颠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忠犬、夜归人
去年冬天某个晚上天气骤冷,寒意渐生,眼前忽然晃动一幅场景。
想到十多年前在老家造办公楼时,有一次晚上从杭州办公室离开已是九点多,驾车疾奔一小时回到半山腰的工地,漫天风雪飞舞,一脚深一脚浅地往里走时,闻声而来的四条大小忠犬低吠着迎了上来,嘴巴各自轻轻叼住我裤管,摇头晃脑,亲热异常。心中一热,脑海里涌出唐朝刘长卿诗中描述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场景,于是,装潢时请中国美院的徐老师创作了风雪夜归人图画,再请人制成石雕置于大楼右侧雪松旁。
光阴似箭,倏忽十几年过去,当年场景犹在眼前。几条忠犬均已寿终正寝。我们把它安葬在附近山坡上,使我仍能时时感受它们的忠诚守护,使风雪中的夜归人感觉忠犬从未远去……

永远的江藻
性格使然,我写文章与平时做事并无二致,都是率性而为,从不曕前顾后,也不左顾右盼,但今天挥笔写生我养我的故土江藻时,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用什么题目时反而有了片刻犹豫。脑子里忽然迸出两句唐诗“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尽管那是触景生情的送别诗,但与我面对江藻湖旧景的心境相近,就用它作题目吧。
智国兄十八年前一篇文章中曾如此描述过我:
“永新兄是一个怀旧的人,也是一个怀乡的人,无论他走得多远,江藻始终是他头顶的一轮明月,那月之皓皓清辉,永远照着他的背影。”
“当他站在杭州和北京的办公室里,隔着落地玻璃,眼前是波光鳞鳞的西湖,是巍然矗立的新央视大楼,但心中念念不忘的,始终是江藻村口的那株大樟树。”
当年首次读到这段文字是在北京的办公室内,我耸然动容。
就以这两段话作结吧!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文章作者,大公报大公网同名纪录片总策划、总制片人、主持人,大公网、浙江日报等众多媒体特约撰稿人,浙江诸暨远征大酒店董事长)
标题:陈永新:江藻,满天风雨下西楼
地址:http://www.sihaijt.com/sxjj/175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