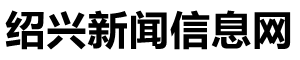序
对故乡江藻的感情,已深入到骨髓。
对儿时江藻场景的亲切记忆、离开江藻时的恋恋不舍、念及至交发小死伤的伤怀、江藻湖边散步时常有儿童指着我“笑问客从何处来”时的感慨……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心中五味杂陈,以至于迟迟不忍动笔。
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忽然有了想写的情绪,于是,一口气一停不停,将积压已久的感情集结成篇,使多年来对江藻的感情有了部分宣泄。当然,较之我对江藻太深沉的爱,仍是挂一漏万。
身为江藻子孙,喝江藻湖水长大又年逾花甲的我,目前能为故乡做的,只有这点了。
许多朋友给我留言或当面说:看到有些情节时,感动泪下。也有人说意犹未尽,建议写续篇。
我原本并无写续篇打算,但今天觉得还是动一下笔,因为在江藻,我们的长辈大都已作古,我们这一代人对江藻的记忆如果再不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江藻的旧时场景就消失在下一代的记忆中了。
为江藻子孙后代留点记忆吧,仅此而已。
大溪坑、大沙滩、肉店、豆腐店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江藻是典型江南水乡的小家碧玉型小镇,有一条被大家叫作大溪坑的溪水以上方的杜月坞山水为源头,蜿蜒曲折,绕过几个村庄,穿过集镇流入浦阳江。那时的溪水清澈见底,农妇淘米洗菜都在间隔着的埠头上,儿时,常看见有人发现溪底的游鱼向下游游去,便手持长竹竿网兜在溪边街上同步奔跑,试图赶到前头将鱼兜住的场景。
蜿蜒的溪坑上架着几座石桥,便于两岸民众通行,而且每座桥都取有名字,我只记得:我们祖宅对面的叫六板桥,那附近一圈也就叫六板桥头。我三四岁时胆小,去桥对面一个婆婆家玩耍,走到一半望着湍急的溪水心中发毛,便趴在桥面上口中念念有词“要勇敢,要勇敢”,一面连滚带爬过了桥。
只可惜,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大溪坑被盖上了厚厚的石板供人车通行。大溪坑的水仍在石板下奔流,不知那游弋的小鱼头顶没有了蓝天白云,是否会气憋得慌。
溪坑流至龙头山脚下位置右侧,有一个道地,江藻人把它叫做大沙滩,我们小时候还未浇上水泥,夏天光脚走在上面,沙子夹在脚指缝中间,滚烫滚烫。
大沙滩是江藻的重大新闻发布及娱乐活动指定场所,用村民的调侃话说,是江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敲锣打鼓迎接过红宝书,挤破头看过电影《三打白骨精》,看着斜背枪支的民兵把一群地富反坏押上台批斗,每念至此,我都心情沉重,因为:饱经风霜的老父亲都是站在被押着的行列中的。
1976年底,我读高一,学校组织会演,我被指定演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在大沙滩台上反来复去念叨自取其辱的几句台词,以至于江藻的小孩子有一段时间看见我就笑骂“王洪文来了”跑开。
从标准像看,王洪文是三七开分头,我们都理着土得掉渣的头型,临演出时,老师一发狠,从食堂里拿来一小勺猪油往我头上猛按岀一个三七分头型来,演出结束累了回家倒头就睡,害得我老娘洗了三次枕头套都没洗干净。
唯一的肉店是小镇老街上最热闹的所在,那是国营食品公司在江藻唯一的肉店,杀猪和卖肉是同一人,叫钱天青,身份是国营职工,另叫几个村民帮手,他当时在江藻小镇上的地位仅次于公社书记,因为每天只杀一头猪卖,后来又凭肉票,所以肉店的木棚门未打开,人群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棚门一卸下,江藻乡亲“天青叔、天青伯、天青爷爷、天青师父”的套近乎声便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天青师父一手拿刀斩肉,一边精准地将肉掷入拥挤在台前的人竹篮中。买到肉的人欢天喜地,买不到的便唉声叹气。
我十三、四岁时有一次向老娘主动请缨要了一斤肉票和八毛钱(那时猪肉每斤六角八分),说我去买肉来。老娘将信将疑,说这么多大人,你挤不过他们的。我到后一看这么多人挤不进去,就绕到最角落人一蹲下从人群中钻了进去,然后猛抓横挡站立起来,钻出半个头来,大喊:“天青伯伯,给我称一斤肉”,那天青伯一看一排大人中突然钻出个小孩子脑袋,吓了一跳,笑骂:小主!是张老师儿子,直头健嗒(意即还蛮利索),便斩了一斤肉掷进我篮里。我拿回找的零钱,拎着篮一路小跑回家邀功,把老娘眼晴笑成了一条缝,连声说:直头健嗒,直头健嗒……
天青师傅喜欢打篮球,球艺却不怎么样。但碍于他的特殊地位,他当中锋一旦运球时,很轻易能被抢断的球对方都不去断,任由他三大步投篮。有一次他运球人家让他,却不料他身子胖,球往前滚了他追不上,直至滚出边线,满场观众也只是齐声叹息却无人敢讥笑。
相对于肉店天青师傅的风光,几步之隔的豆腐店就稍差一点。豆腐店是供销社的,里面唯一一位磨黄豆做豆腐的师傅叫钱吉根,江藻老小都叫他吉根豆腐。他是非常辛苦的,傍晚七八点钟一个人肩上拴着绳索,推动着大石磨磨黄豆,昏暗的灯光下,那驼背的身影沿着磨盘不停转圈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豆腐店没肉店拥挤,但也算热闹。彼时的人们还都纯朴,因为供求基本平衡,没有肉店里大都买不到的担忧,所以,大家都按先后到的顺序,将碗盆等盛器放在豆腐店棚门前,待吉根师傅褪下棚门,便逐一点碗盆主人的名字,将豆腐放了进去。
大溪坑、大沙滩、肉店、豆腐店,已是江藻老一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无论走得多远,想起那场景,淡淡的乡愁便在心中弥漫开来……
锦芳老头、高踏步粮站
在江藻东沙塘边上,曾有一处气势恢宏的民国建筑,外面几十级高高的石阶上去,推开双扇门上有硕大铁环的木门,深宅大院便映入眼帘,院内画栋雕梁,飞檐斗拱,二层大楼曲院迴廊庭院深深,中间青石板院子正中一口深井,内壁厚厚的青苔似乎在诉说历史的沧桑。
这是江藻在外谋得民国时期富阳县长一职的钱锦芳老人的私宅,据说他在富阳任上曾为百姓谋不少实事,卸任后去四川谋职前,从富阳购得一批建筑材料和已雕刻好的木牛腿,满满两船装到江藻村外浦阳江陈潘埠头,花两年时间造成江藻最气派的民国建筑。
后来世事变迁,锦芳老头死于非命,那外墙青灰色的江藻标志性建筑便充公成了姚江粮管所江藻粮站。
少年时,那粮站是我每月必去一次的地方,因为老娘和我是居民户口,每月每人凭票供应的四两菜油是全家视作宝贝的东西。老娘每次把那油瓶交给我时都要叮嘱:打油时把瓶在打油口多站三分钟,待油滴净才走,至少可以为她多炒一碗菜。所以,我每次都要两眼紧盯着那油吊子倒下后的滴油口,直到确认已滴不下油来才离开。
九十年代初,粮管所改制,要将这承载着江藻几代人记忆的建筑出售,我闻讯后非常想把这幢楼买下来留个念想,但未料遭到已搬到县城居住的老父亲的坚决反对,我问为何?老父艰难地一字一顿说:江藻留给我们是几十年屈辱的记忆,你还想回去吗?面对老父如此激烈反应,我只得放弃。
也许老父是错的,人对于故园的感情是与生俱来割不断的,不因人、因事而改变,而且以当年的政治气氛及老父的旧政府官员身份,恐怕到哪里境况都不会比江藻好的。
也许我是错的,老父在江藻的四十多年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以致我们无意中去触碰一下当年的屈辱话题,他都会无端地发火。
后来,该建筑物被他人买走并夷为平地,另造了现代住宅,但我每每走到那地方,就要浮现起那锦芳老头的高踏步台阶,那油瓶里的八两菜油,有时怔怔站在那里,怅然若失。
一个时代的印象都留存在记忆深处,回不去了,莫名伤感。




粮站拆除时,有心人保存了当年的部分画栋雕梁
华华阿哥、关心叔、林潮伯
由于老娘教书,我未上小学前无法带在身边,便将幼年的我托村中其他农户代为抚养,最初是上文写到的下陈自然村的乳娘,后来又转到钱家宅自然村的华华阿哥家。
华华阿哥一家三代良善,把我这个搭伙的小孩真真切切当成了自己人,任由我在大饭桌上爬上爬下,待菜上来我嘴馋先用手伸过去拿着吃,他们也不怪我。
华华阿哥长我七八岁,放学后天天背着我四处玩耍,下溪抲鱼摸螺蛳,上树抓知了,摘桑椹,玩得精疲力尽便趴在华华阿哥背上睡着了背回家。
有一次华华阿哥把我背到学校,学校开批判会,我在他怀里睡着了,奶奶四处找我不着,以为我掉在池塘里淹死了,拿竹竿去池塘里拨弄也不见,急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后来找到学校向我老娘告急,刚好学校批斗会散场,华华阿哥背着睡眼惺忪的我出来,奶奶看见,转忧为喜,却害得华华阿哥莫名其妙挨了奶奶一顿竹棒。
华华阿哥大名钱建华,后来考上了卫校,毕业后在诸暨中医院干到退休,有时晚上散步碰到,远远喊我乳名,心中的暖意,溢满全身……
除小时候寄养的两户人家,是从来没人叫我也不知我乳名的,我在自己家里也没乳名,现在两户人家老人都已仙逝,年逾花甲之人,碰到绝无仅有的叫我乳名的人,真是亲切、温馨,儿时场景顿时又涌上心头……
关心叔是我老父亲好友,因腰部疼痛被老父治好而成为朋友。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我们家是很少有人愿意来往的,关心叔是为数不多的从不避嫌三天两头往我家跑的人。有一次他从浦阳江抓来一条白条鱼就屁颠屁颠往我家送,那鲜美的味道至今难忘。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家中的蕃薯苗拿到集市上要被没收,关心叔夫妻胆大,拿到隔壁萧山的临浦去卖便没事,所以他经常拿蕃薯苗去临浦贩卖,往往头天晚上到我家,趁着夜色将我家的蕃薯苗拎走,第二天便将几元几角毛票整整齐齐叠好交给老父。
有一次,关心叔为我从临浦带回一双塑料凉鞋,四角五分钱,老父要他从我家蕃薯苗款中扣除,关心叔不肯,两人推来推去,关心叔唯一一次对老父亲红了脸,大声说:永新是我小侄儿,我送他一双凉鞋总也送得起吧?
老父这才说好咯,并使劲拍了拍关心叔肩膀。
关心叔是乐天派,是那个沉闷的时代少有的幽默之人。
有一年正月初二,我十三岁,向老娘要了一包香糕,说给关心叔去拜年,走到他家,他刚好准备去丈母娘家拜年,便自言自语说:今天这个小毛脚女婿来拜年了,我这个老女婿丈母家拜年去不成了。
见我莫名其妙,关心叔又继续调侃:小主!甭怕难为情咯,三个女儿,挑哪个做我女婿,自己话一声。
以至于几十年以后,关心叔叫我去吃饭,我也不忘调侃他:你当年在我小屁孩面前做白市好人,三个女儿,一个也没许给我。
林潮伯也是因手脚风湿病被老父医好成为我家常客,我在操场上打篮球,远远看见他拎着竹笋、青菜从小山坡上向我家走来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在那个人人自危、对于像我们这样被贴上标签的家庭,大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关心叔、林潮伯以及大孤山的汤根叔、本村的云水叔等几个经常出入于我家的叔伯,给我们这个不时被凄风苦雨侵蚀的家庭所带来的温暖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
人情、人性,当年珍贵。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更珍贵。
今借小文一节,向已作古的几位叔伯致敬!
郭老太太
我江藻老镇上,像我这样六十岁以上的人,一定记得有一位老妪——郭老太太。
我们读小学时老人家已六十多岁,那时的农村贫穷落后,六十多岁已是老态龙钟,江藻唯一的青石板老街上常见一位穿着大对襟青衫、满头灰白的老太太柱着拐杖蹒跚而来,无论何人,见了她都毕恭毕敬为她让道,比她稍小点的大声叫她一声郭老太太,像我们这些小孩,只敢远远向她行注目礼。
老人柱着拐杖,间隔着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伴随着胸前一大串毛主席像章和另两块我从没见过的奖章的撞击声,叮叮当当,成了江藻老街上常见的风景。
懂事以后,村里的大人告诉我:老人家姓郭,是外地人嫁到江藻的,并为夫家生下了两个儿子,不久,丈夫病亡,老太太独自拉扯两个小孩艰难度日。
好不容易把两个儿子养到二十来岁,朝鲜战争爆发,征兵任务下到村里,两个儿子都应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到了冰天雪地的朝鲜,而且永远地长眠在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青谷之中。
从江藻这个江南小镇走出去的敦厚小伙,回来时只剩下两张薄薄的纸片和铁片(军功状和勋章)。
老人家几乎哭瞎了眼,只能看到很近的地方,五十岁不到便柱起了拐杖。
由于志愿军烈属的特殊身份,老人在江藻小镇上受到特殊的尊重。记得有好几次,老人经过那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猪肉店、豆腐店门口时,只将手中的竹篮晃得一晃,大家便自觉让开一条小道,让郭老太太笃悠悠买完猪肉或豆腐离开后,再立即又挤作一团。
老人家对人很和蔼,但是,对那两块小铁片却视若珍宝,只允许亲近的人凑近去看,但绝不允许人家触碰。
想想也是,儿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两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变成了两块冰冷的铁片,这铁片已成了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怎么肯让人触碰呢?
遗憾的是,由于夫家已无其他亲人,彼时江藻父老也无证据、档案意识,当年的两块勋章和纸片所记载的江藻子弟为国效命的历史,随着老人家的去世都湮没了。
我也只是七、八年前偶然在一份诸暨当地编的资料中看到有两位江藻东沙村两位在朝鲜牺牲的兄弟俩名字,应该就是郭老太太的儿子。
瘦小、苍老的郭老太太,声音也已含混不清,但有一次,那瘦弱的躯体里突然发出一声暴吼,使所有人都被镇住,也使我这个长大后听江藻父老绘声绘色说起此事的人对郭老太太充满了敬意。
那是风雨如磐的政治动荡年代,当时,被打倒的走资派、诸暨老县长何文隆被县城里的造反派押着到各公社轮流批斗,六十来岁的老县长戴着高帽被押进大沙滩的高台上批斗,老人精疲力尽,人几乎要瘫倒,但凶神恶煞般的民兵仍拎着他后领不让其倒下,台下一众村民于心不忍,但又不敢出声,忽然一件青衣大襟衫的身影颤颤巍巍上得台来,一手拿着一条长凳,一手端着一碗茶水,径直走到何县长面前,大声说:你坐着好了,先把茶喝下去。
台上一干人傻了眼,不知这大逆不道的老妪是什么来头,那县城来的造反派头头刚要发作,当地公社干部凑到他耳边嘀咕了几句,并指了指青布衫上那两块特殊的铁片,那人只得悻悻作罢。
老县长满怀感激地望着老人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把茶水喝下,一屁股坐倒在长凳子上,眼泪扑簌扑簌掉到台上……
郭老太太似乎还余怒未消,再指着台上一干目瞪口呆的人说:
“他介大年纪了,你们罪过怕不怕咯?”(江藻话不怕可怜吗之意)。
台上台下都鸦雀无声,江藻父老都满怀敬意目送郭老太太拿着空碗晃晃悠悠走下台来。
后来,这位穿着草鞋走遍诸暨山山水水,对诸暨水利建设居功至伟的草鞋县长被平反并享受诸多荣誉。我想:他一定会记得:在他人生的至暗时刻,有一位大义凛然的郭老太太为他端上了如饮甘露的茶水和供他喘一下气,歇一下脚的长凳。
当然,他一定也会记得老太太胸前那两块护身符: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功章!
任何时候,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行动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温暖!
这样正直的老太太,是足以让江藻子孙引以为傲的!
发小、发小
从小一起在江藻玩大,朝夕相处的伙伴,到了晚年仍然走动的终究为数不多了,钱博士算一个。
他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代正宗博士,发的博士学位证书号码是百位数,比起现在满大街的博士,含金量高了不少。
博士发小五短壮实身材,豁达幽默,宠辱不惊。我俩婴儿时即为伴,现常同漫步江藻湖夕阳余晖下,至今整一甲子矣。
幼时两者老娘过往甚密,为便于照看,常将两人置于同一摇篮内,两岁后渐见端倪,我瘦长,他矮壮。高中毕业后他一路读至博士,我高考落榜进城务工,从此人生轨迹迥异。
每相逢,即以取笑、调侃、自嘲为乐。某日说起小时情形,我曰:两岁后我娘见你娘不敢比(儿子)壮瘦。他即答:三岁后我娘见你娘不敢比(儿子)长矮。我又称:高中后我娘见你娘不敢比(儿子)读书。他又答曰:到如今我娘见你娘不敢比(儿子)钞票。
言毕,两个小老头皆抚掌大笑。这博士,书算读通透了。天下人,熙来攘往皆为功名利禄,想透了,过眼云烟,多大点事呀?
另有一位发小马龙校,自幼家贫,是遗腹子,倍受歧视,与我却过往甚密,有一次我已在茶厂工作,他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给我送自家山上的水蜜桃,到了县城下起大雨,待他气喘吁吁踏进茶厂,浑身已是湿透。
后来他当兵去了芜湖,复员后在那里娶妻生子。听说他病了,我也特意开七八个小时车去看过他。
十多年前一个傍晚,忽然接到他的电话,说已入弥留之际,住入杭州117医院,希望见最后一面,我和钱博士晚上匆匆赶到那树木参天的部队医院,顿感一阵寒意袭来,见到龙校,他脸色蜡黄,说话已很费劲,我在他病床床沿坐下,知道已经是最后一面,心中凄然。
后来龙校迸出最后一句话:你们好回去了,碰到谁谁问个好,江藻我回不去了。
待他再回去时,已成了小时候玩耍的山头上的一处隆起的土堆。
那天,我和巨炎去看了他,上山的时候原本阳光灿烂,走到半山腰忽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我们伫立在土堆前,久久无语……
发小死的死、伤的伤,触目伤怀,如鲠在喉……
永远的故乡
感谢网络这一现代传播手段,使我心中积压已久的对江藻的感情得以充分宣泄。
江藻,是我永远的故乡,永远的精神家园,用智国兄多年前描写我的话说:无论他走到哪里,故乡始终是他心头那一轮明月,那月之皓皓清辉始终照着他的背影。
江藻沉寂已久,重整河山终有时。
搁笔之际,耳边忽然回荡起张明敏那如泣如诉的歌声: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把它献给至亲至爱的江藻吧!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文章作者,大公报大公网同名纪录片总策划、总制片人、主持人,大公网、浙江日报等众多媒体特约撰稿人,浙江诸暨远征大酒店董事长)
标题:江藻,重振河山终有时
地址:http://www.sihaijt.com/sxjj/17599.html